Mockingbird • 漫长的告白:欲言又止,各怀心事
1 语言
似乎近段时间以来,“语言”在东亚地区的作者电影里发挥着愈发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不同母语使用者之间交流活动的刻画。譬如,滨口龙介就长期将不同媒介的“讯息”(message)作为自己的电影母题,并在《驾驶我的车》那里达至包括身体语言(手语)在内的“跨语言交汇”的顶峰。朴赞郁的最新作《分手的决心》同样塑造了一对韩语与汉语之间的沟通罅隙,并且随之隐约映射了两个国族的历史文化身份。至于张律的这部《柳川》,亦是直接彰显了汉语(包括北京话与非北京话)、日语、英语以及身体语言(舞蹈)的并置局面。
借用二十世纪以来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说法,我们或许亦可以把上述现象不完全归纳为东亚世界作者电影的“语言学转向”。简单从共性来看,无论滨口龙介、朴赞郁还是张律,“跨语言”的文本设置大都牵涉现代版本的“巴别塔”寓言之意:孤独而微渺的个体,短暂而脆弱的集群。实然的语言屏障阻断了共同理解的彻底达成,后者终究滑落为现实的奢望,是先天的注定失落,是先验的不再可能。

大概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这部电影的最终定名不再延续张律的经典“二字诀”,但就作为母题要素的“语言”角度来看,原名《柳川》显然优于《漫长的告白》。“柳川”既是人名又是地名,既是中文语音的“Liǔ Chuān”又是日文语音的“Yanagawa”。换言之,“柳川”一词本身即指向一种多义性、含糊性与不确定性。朦胧感由之从片名出发,顺着时间和意识的双重流动逐渐蔓延,最终通过难以名状的方式笼罩着难以名状的东西。根据电影结尾的录音,死去的立冬确乎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痕迹,实则是柳川的歌声被返还给了她自己。这到底是生命情态的悄然安放、再度悬置还是长久惘然呢?抑或答案从来不止一种,抑或从来没有什么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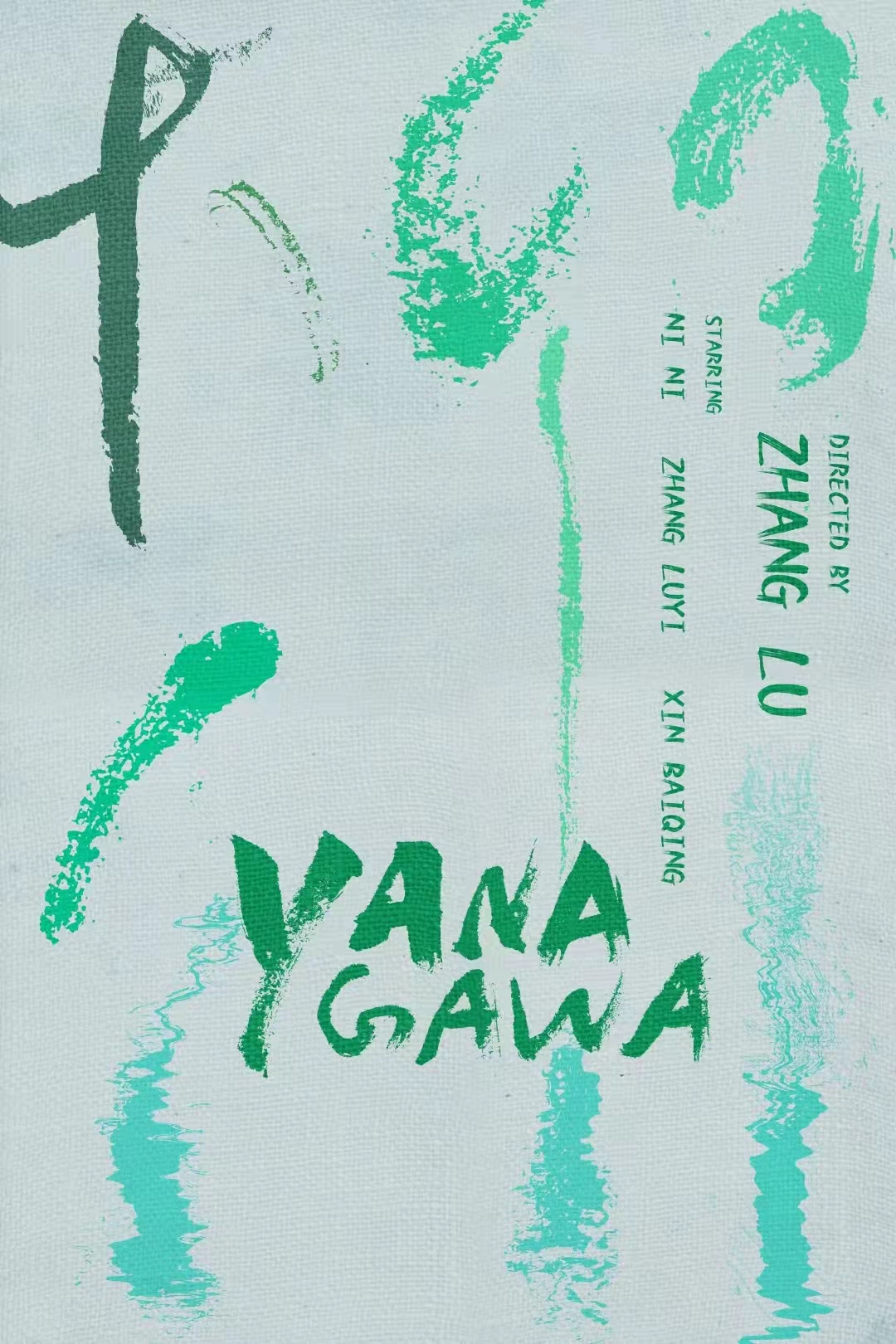
总之,不同语言尽管如川流一般在电影里汇合,但是似乎终究无法像后者那样交融为同一片海。大概因为人终究不同于水分子,人类语言所标志的异质性势必超越相等架构的H2O。鲁迅《而已集》曾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句话已是在同种语言的情境写下,更何况村上春树所言“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呢。相应值得一提的是,《柳川》谈到了日裔英籍作者石黑一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石黑一雄的“异乡性”与张律的创作姿态颇具亲缘,二者似乎共享着跨文化这一类别的文本调性和书写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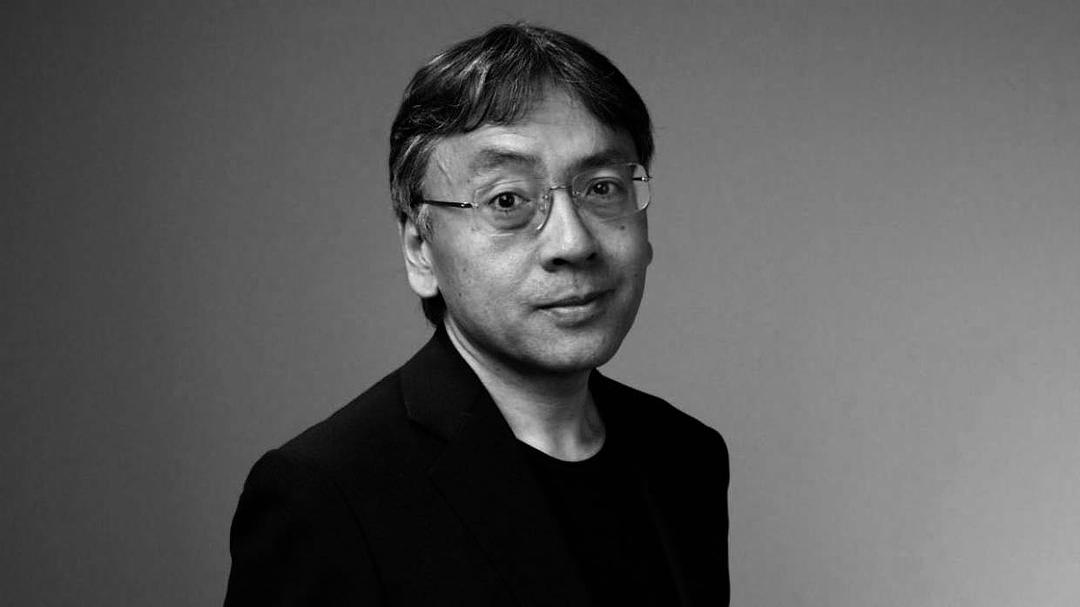
2 不言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5.6说道:“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换言之,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语言的终结之处几乎就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不可言说的东西即是超出世界的东西,反之亦然。于是乎,《逻辑哲学论》最后一句(命题7)定言为:“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凡是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必须在沉默中略过。)

《漫长的告白》之所以“漫长”,不仅系于从过去到现在的自然时间之延宕,而且还暗示存在着某些未曾被明言直说的部分。影片最初,立冬就自我掩埋了身患绝症、行将离世的讯息,如同泽维尔·多兰《只是世界尽头》里的那位返回故乡的剧作家Lious,他们的“必然缺席”都从一开始便被钉入了自我历程的终点,他们的在场身份是“不在场者”,他们的在场状态是“向死而生”。总之,影片人物最初就是从“不言”里走来:立冬对于生理病症沉默,立春对于中年生活沉默,柳川对于离别动机沉默。

面对“柳川突然不辞而别”这一往事,不同的人怀揣着不同的想法和解释,好像各自面向的从来就不是同一个对象。立冬以为是因为自己那时的贸然侵犯(“摸了阿川的胸”),立春以为是由于自己当初的移情别念(“把阿川给甩了”),柳川却说当初离开只是家庭生活出现变故的原因(“随母亲投靠英国亲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缘故呢?还是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缘故?抑或是真正的“缘故”从来无法明确说出?
除了人物之间的相互不言,张律亦以“未曾明说”的方式悄然显示了两个男人之于柳川的意义,其关键就在于人物的命名。按照“春夏秋冬”这一通常称谓,“立春”处在“立冬”之前(正如哥哥年长于弟弟),春天亦比冬天更为和煦,更加适于“柳”的生长、“川”的流动。于是乎,柳川确曾与立春建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然而,如果依照一年的月历变化,立冬所昭示的冬季(12月至2月)却又先于立春所昭示的春季(3月至5月)。联系柳川初到北京的经历,由于北京话说得不标准(注意:这里又牵涉到了语言/语音元素),她遭遇了多数本地孩子的嘲弄和排挤,除了立冬对于她的义无反顾的维护。从这个意义来说,“立冬”实则处在“立春”之前,在柳川的生命历程里,弟弟的在场先于哥哥的在场,尽管后者的爱意更为浓烈,前者的情愫更为折叠。

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一处虽是“不言”但为“同契”的段落,那就是柳川与居酒屋老妇人的相处时空。一方使用汉语喃喃自语,另一方使用日语循循回应。二者语言的互不相符是为实质的“不言”情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某种超越语言的共通感绵延于这两个女人之间。实际上,老妇人与柳川以及柳川与女学生(中山大树女儿)的人物交际都实现了“超语言”(而非“跨语言”)的进一步理解,一种存在于女性之间的独特联结以三个代际为标志被张律写下。与之相比,男性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不言”似乎仅仅是遮蔽,仅仅是沉默本身而已,似乎更难存在“超语言”的机会或者潜能。

3 心事
语言的“天然”隔膜,不言的“应激”反应,几个人物常常欲言又止,一个根本原因(或可简单比附为符号之下的“原质”)恐怕在于他们全都各自怀着自己的心事。“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无法言说的”)既指向客观的无能为力,也包括主观的不愿提起。柳川、立冬和立春,三者内部一并嵌入着难以吐露的“亏欠”、难以释怀的“症结”。

对于柳川来说,因叫声而被排异的“乌鸦”既象征着立冬,也象征着自己。当初因为北京话而成为少数者,唯立冬甘愿一起陪同。时至最后,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与立冬本是最深意义的“同路人”,是多数的他者、是中心的剩余。可是,如柳川自己所道出的,面对那只离群的乌鸦,她所做的却亦是“无动于衷”而已。面对同样形单影只的立冬,她实则难以施予太多,匮乏者不曾填充匮乏者。
对于立冬来说,他的亏欠主要凝结为那一次禁忌的触碰。多年以后,当初后海的皎洁月光仍然在被自我亵渎,挥之不去。柳川的离开被他意向为一次逃避、一次失望、一次责罚。从此开始,无邪的少年维特沦为有念的少年维特,起初的崇高感沦为长久的罪恶感。然而,当再度提起这件事时,柳川却表示不再记得了。到底是真正忘却还是刻意避开呢?我们(包括立冬在内)恐怕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认的是,立冬的此刻心情大概和写作回忆性散文《风筝》时的鲁迅一般,那个过往的被亏欠者似乎对于亏欠本身都不再记得,对于亏欠者的罚与恕又从何谈起呢?“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说谎罢了”,因为被亏欠者的不再记得永远无法确认,永远停留于“似乎”。

至于立春,他的心怀芥蒂可能显得更为直白。早早投入稳定的个人生活,工作、结婚、育女,他又一次站在多数者的行列,正如曾经身处北京话使用者的多数。从根本上看,他与立冬、与柳川都并非一族,嘲弄弟弟“脑子不正常”是因为自己“脑子太清醒”,纵使尽显风流潇洒,心底却是对于不确定性的畏惧(象征场面:身处异乡床榻却fail in erection)。简言之,他的心事正在于绵绵的纠结,徘徊于安稳与波折之间、家庭与旧情之间,他的“多数者”身份仿佛亦映照了生活里的最大多数人。
最后的最后,清亮的歌声似乎不断绵延,有人回归了日常,有人回归了故土,有人回归了大地。“告白”(confession)不仅指向爱意,同时指向悔意,后者与所谓“告解”或者“忏悔”相关。正因为“爱的宣示”与“罪的自述”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方才欲言又止,我们方才各怀心事。如果一定需要跨过语言的界限,大概只能“以不成声音的声音,以不成话语的话语”(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

